鹭风报 国内统一刊号 CN-35(Q)第0003号
鹭风报 国内统一刊号 CN-35(Q)第0003号
发布时间:2020-01-10作者:张老六来源:选自《华人周刊》点击量:13902鹭风报1447期05版 专题
2000多年前,一位名叫王昭君的湖北姑娘远赴大漠,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承载着两个民族和平的重任。逝水移川,千百年后另一名湖北姑娘亦因气度与贡献,被著名作家丁玲喻为美国的“昭君”。
她的名字叫聂华苓,一位被誉为“世界文学组织之母”,也是唯一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。
在她家客厅,包括汪曾祺、陈映真、白先勇、王安忆、迟子健、毕飞宇等,以及全世界1400多名的诗人与作家,都曾在那里餐宴饮酒、肆意畅谈文学。其中甚至出了两位文学诺奖得主:一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;一是中国作家莫言。
打开聂华苓的自传《三辈子》,宛如看到一幅浩浩荡荡的历史画卷。国家战乱、颠沛流离、永远的乡愁。
现年95岁的聂华苓,漂泊了近一个世纪,从汉口到北平,从大陆到台湾,从台湾到美国。她说,“我是一棵树,根在大陆,干在台湾,枝叶在爱荷华。”
循着这条“树根”,让我们来见识这位气度不凡、侠肝义胆的女子。

抗战时期的聂华苓(后中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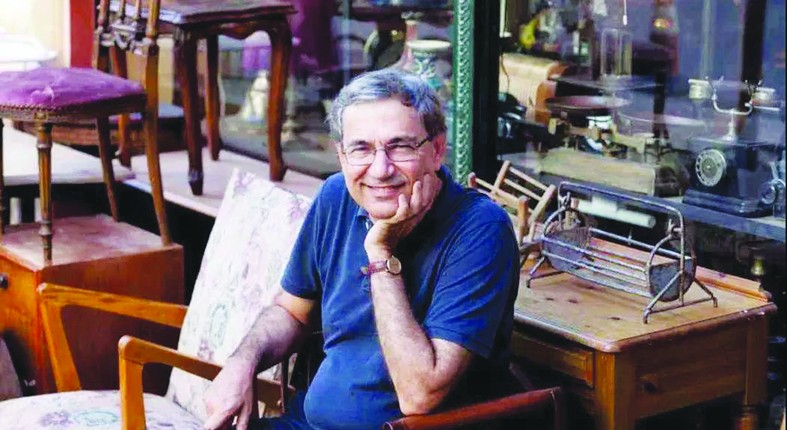
土耳其作家帕慕克

中国作家莫言
异乡人
聂家祖上算是钟鸣鼎食之家。聂华苓的祖父是中过举的前清文人,原本是要上任当县长的,没想到赴任途中,武昌起义成功,他只好又坐着轿子回来了。
父亲聂洸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,在桂系担任要职,一度遭国民党追捕。桂系被蒋介石击垮之后,一家人在汉口的日本租界住下来。只是当时兵荒马乱,谁分得出桂系嫡系?红军长征经过时,直接把聂洸当作蒋家的人给办了。聂家就此散了。
讲起来,聂华苓这一生都在流浪。13岁以前,她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。那时,她和弟弟为了吃上一根雪糕,需要走过日租界、德租界、法租界、英租界、俄租界——英租界的红头洋人,拿着木棒打得中国的人力车夫和叫花子跪地求饶;日本兵在日本人开的妓院里高声歌唱,其间夹杂着高丽女人的媚笑。
半殖民地的凄惶画面,在聂华苓幼小的心灵深处刻下了一道道永难磨灭的伤痕。
中日战争爆发后,眼看武汉就要被日本人占领,母亲带着五名幼子逃亡至乡下避难。
母亲孙国瑛是个开明人,在聂华苓的自传小说《三辈子》里,她这样描写母亲:一身黑缎旗袍,长长的白丝围巾,围着脖子闲搭在肩后。玳瑁黑边眼镜,衬出白皙的脸蛋。一脚在身后微微踮起,脚尖仍然点在地上,半转身微笑着,要走又走不了的样子。
这样的新式女性,自然知悉接受教育的重要性,即便外头烽火连天,她也执意要送女儿到外地求学:我母亲说不行,你非去不可,你一定要读书的……走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岸上已经相当远了,就哭啊哭啊哭啊,我母亲站在那里也哭。
母亲的气度与倔强,无疑对聂华苓后来的性格造成深刻的影响。彼时仅14岁的聂华苓,在母亲毅然决然的目光和泪水中,就这样流浪下去。
求学的日子困顿至极,有时一天只啃一个硬馒头,有时要跟狗抢食物。糙米、稗子、石子、沙子混合而成的“八宝饭”都成了人间美食,聂华苓甚至一度染上疟疾。
只是,眼见大好河山惨遭日本人蹂躏,小小少年早已忘了身体的苦,她的心中犹如倒入了黄连,痛苦至极。为了不当亡国奴,再苦也要一路奋战。
聂华苓加入了排山倒海的抗日活动中:慰问抗战的伤兵,为他们唱歌,代写家书……那一路上所见的名山胜水,更是让她增加了爱国的砝码:“我年青的日子,几乎全是在江上度过的。武汉、宜昌、万县、长寿、重庆、南京……我在江上活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战乱。”
从汉口到北平,从小学到大学,从纯真的孩子到挨冻受饿的流亡学生,总算迎来了抗战胜利。
风雨坎坷中,聂华苓与国立中央大学的同学王正路结婚了。她以为找到了安心的归宿,那个时期,她甚至以“远思”为笔名,发表了一篇讽刺性文章《变形虫》,开启了她的创作生涯。
然而,婚姻也好,局势也好,都无法让聂华苓停下流浪的脚步。王家的大家族,需要媳妇日日向长辈请安奉茶,繁文缛节压制了聂华苓的自由性格,她喟叹:“我在那个大家庭里,只是一个失落的异乡人。”
而婚姻之外,内战爆发,幼年失怙的情形仍历历在目,聂华苓内心充满了恐惧。
1949年,24岁的聂华苓拖着母亲与弟妹,一家人到了台湾。“流浪”变成了“流亡”。大陆成了她永恒的乡愁地标。
 1979年,萧乾(左一)是第一位被邀请到爱荷华的中国作家
1979年,萧乾(左一)是第一位被邀请到爱荷华的中国作家
台湾文学的火种
然而,那座小岛,并没有给聂华苓带来风和日暖,而是一片肃杀之气。到了台湾后,原本寄予希望的婚姻触礁了。出身大户的丈夫根本经不起风雨,“结婚15年,共同生活只有5年”,婚姻名存实亡,家庭的重担全落在了她身上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,聂华苓进入胡适发行、雷震主持的《自由中国》半月刊,任文艺栏主编。
当时台湾的文学环境政治色彩非常浓厚,不仅写作者被监视,文字也要被审查。而且,很多人为了赚取微薄的稿费,都可以写出配合“反共”的文学作品。但聂华苓不一样,其父一生困于政治斗争,终致家庭离散,这使她对政治敬而远之。
为了避开政治,她将自己主编的《自由中国》文艺版,打造成纯文学天地。这简直就像是浑浊的湖泊涌出一股清泉,湖底的一些奇珍异石顿时袒露在阳光之下。
现在成为经典的很多作品,譬如: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,梁实秋的《雅舍小品》,还有柏杨的小说和余光中的诗,都一一在她手上登场。可以说,1950年代整个台湾文学的火种能够被点燃,都归功于聂华苓和林海音这两位女性。她们二人在威权时代开风气之先,提倡纯文学创作,为整个中国的文学做出了贡献。
聂华苓在台湾的倏忽15年,却受到文史家一致好评,也是聂华苓一生中编、写、译成果最丰硕的黄金时期。她的《失去金铃子》,和林海音的《城南旧事》,以及徐钟珮的《余音》,并称为三部带有自传色彩的杰出女性成长小说。
同时,《自由中国》在雷震的带领下,除了发表针砭时弊的社论,也刊登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。
可惜,当时的台湾文坛和政治环境过于险恶,“白色恐怖”笼罩了全岛。因为雷震刊发了一篇夏道平写的《政府不可诱民入罪》,被诬陷“知匪不报”,以“煽动叛乱罪”坐牢十年。
随后《自由中国》被封,聂华苓身为编辑虽躲过牢狱之灾,却被孤立,终日受到监视。彼时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:《自由中国》和前辈们蒙难;弟弟汉仲在一次例行飞行中失事;母亲过世;婚姻和经济陷入死局。
聂华苓的第二个落脚处就此断裂。直到聂华苓38岁那年遇到的第二任丈夫,保罗·安格尔。

右一林海音,中间聂华苓,左一琦君

聂华苓和安格尔
国际写作计划
安格尔对她一见钟情,他在回忆录中写道,“台北并不是个美丽的城市……但有华苓,看她就够了。”
聂华苓对这段婚姻的评价,是“我们的婚姻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美满的婚姻。”他们婚后在爱荷华筑起爱巢,一起划船、烤肉、谈文学,与鹿和浣熊做伴,神仙眷侣也不过如此。
此时,聂华苓学会用另一个视角看世界,她意识到,过去的生活虽然艰辛,但她对世界的认识却非常的片面:“在这儿,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峡两岸的社会,可以接触世界各国的作家和作品,这使我的视野扩大多了,感情冷静多了,看法客观多了!用‘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’来说明我的过去,大概是正确的。”
过往的痛苦与恩怨,终在时间的力量下渐渐消融。随之涌上心头的,是她那份岁月沉淀后的气度与侠义。
彼时,安格尔聘请她到他的“写作工作坊”教中文。有一天,他们在河上泛舟,聂华苓突发奇想,建议安格尔将“写作工坊”改成“国际写作计划”(简称IWP)。
安格尔听了,忍不住大叫“疯狂的主意”,要是改成国际写作,每个作家光是吃、住、路费就要好几千美元啊!
然而聂华苓却锲而不舍,他们先是得到爱荷华大学的赞同,接着到处写信,拜访,从私人到大企业,终于募得300万美元的基金。
接下来几十年,我们看到地球上不同肤色、不同语言,不同种族、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,神奇地在爱荷华相遇了。
“写作计划”每年邀请各国作家赴美访问,透过演讲、讨论、旅行等方式,让作家们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技巧得到冲击和对流。由于时代的局限性,当时大部分作家都带着狭窄的视野,但通过交流,发现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不同的人,回国后他们的世界观都拓展了。
他们以文会友,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与芥蒂。譬如,以色列作家和埃及作家从一见面就往对方脸上扔杯子,到四个月离别时,却在机场抱头痛哭;伊朗女诗人台海瑞与罗马尼亚小说家易法素克之间产生了爱恋;第一次出国门的中国作家丁玲握着美国诗人桑塔格的手。
丁玲回国后在《访美散记》中写下:她看到的美国,与过去听到的“帝国主义”“垂死的资本主义”大不相同。美国有超级市场,有分期付款的购房方式,“做的是今天的工作,花的是明天的钱,还的是昨天的债”,汽车多到停车难和修车烦,等等。
5年后,丁玲过世了,她写下的这些,20年后在中国通通实现了。而她所见识的一切,都是聂华苓为她提早打开了看世界的窗。
1976年,聂华苓和安格尔被世界上300多位作家联名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;1982年,两人一同在大西洋城获颁“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”。
身为中国人,聂华苓最牵挂的还是那些用汉语写作的作家。彼时,中国作家想出国,都会面临语言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。为了让中国作家参与国际写作计划,聂华苓自己每年都捐款。
几十年来,“写作计划”共邀请了世界各地作家1400多位,而汉语写作的作家,就占了100多位。很少有人像聂华苓这样,文友遍及两岸三地,能拥有这么多知名作家的友谊。
在国际写作交流上,聂华苓不遗余力;在个人作品上,除了翻译作品,她坚持用母语——中文创作。《失去的金铃子》《桑青与桃红》《三辈子》等等,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她回归心灵故乡的途径。
这位湖北的“昭君”,为华文文坛以及整个世界文学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 严歌苓就是受益于“国际写作计划”其中一位
严歌苓就是受益于“国际写作计划”其中一位